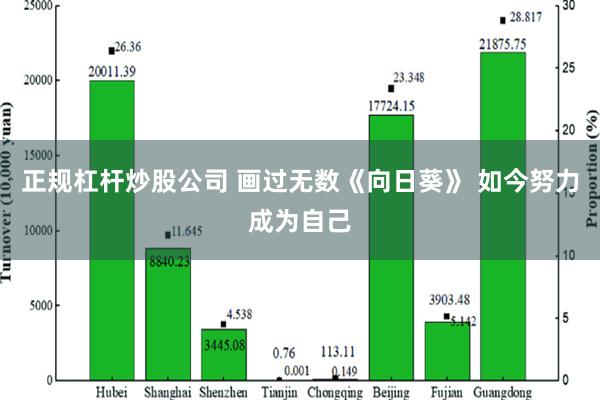
昏暗逼仄的空间里,像晒衣服一样晾着几千幅“梵高画作”,赤膊光膀的男子手托调色板弯腰从画下走过,用画笔挑起深群青和普蓝颜料,挥斥成《星月夜》中旋转卷曲躁动的星云……
在深圳大芬村,因为大量临摹梵高的作品,农民画工周永久和赵小勇被冠上了“中国梵高”之名,一部以他们二人为主角的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,让无数人将探究、心酸、鄙夷、敬佩、感慨等各种色彩的复杂目光投向这里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,赵小勇和周永久二人的生活轨迹不尽相同,但在当下,两位“中国梵高”似乎殊途同归——从临摹复制到原创画作。近日,我们来到大芬村,试图走近这两位“中国梵高”。
以最快的速度产出“世界名画”
如今,坐落在深圳龙岗的大芬村依然热闹,这个占地仅0.4平方公里的小村落,因“中国油画第一村”的头衔招徕了不少原创艺术家,当然,也有许多游客为了“中国梵高”慕名而来。
某个上午,大芬村一间并非位于主干道的50平方米房屋内,刚吃完肠粉从家里溜达20多分钟来到工作室的赵小勇拿起画笔,开始构思自己的新画作。而另一条街上,周永久正一边拿着茶杯喝茶,一边欣赏着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徒弟正在画的风景画。
1991年,17岁的周永久第一次踏上了大芬村的土地。在跟着师傅学画画之初,往往三个月里他都只盯着一幅画,不断临摹、修改,直到把每个图案细节都刻在心里。后来,他开始临摹梵高的作品。
1994年,在人潮拥挤和商客云集的广交会,周永久手中的《星月夜》《向日葵》《鸢尾花》等15幅临摹的梵高画作,引来了外国商人的目光。在这里,他收获了人生中第一笔正式订单——3个月,交付1万幅梵高画作。
面对庞大的订单量、难得的机会和紧迫的时间,他和师傅叫上师兄弟们一起来画。一个学徒负责调颜料,一个学徒负责订画布,“他负责天空,她负责花瓶,我负责最后修改定稿”。
21个人流水线式操作,以最快的速度产出一幅幅“世界名画”。最终,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,他们完成了8000多幅画作。
1997年,在周永久成立工作室的次年,25岁的赵小勇也来到了大芬村。
早在1989年,赵小勇就来了深圳,在工地运过泥沙,进过电子厂流水线,“什么都做过,甚至睡过马路。”机缘巧合之下,他跟着大芬村的师傅正式学起了油画,临摹起梵高的作品。
“中国梵高”代表的是大芬村画工
1996年六七月份,周永久成立工作室后接到第一笔大单,来自三个客户的五万幅画作。这一次,流水线上的“画工”增加到了37人。
在后来的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中,再现了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——
700多平方米的套房里,上万幅画作像衣服一样被密密麻麻地晾在空中,天气再炎热也无法开风扇。12点起床吃饭后开工,干到六七点,晚饭后休息15分钟接着干,直到凌晨吃点宵夜,画到四五点收工……他们像一个个流水线上的机器人,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动作。
这部片子耗时6年,由摄影师余海波和女儿余天琦拍摄,于2016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(ADFA)首映后,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。
如今回过头看这部片子,周永久说,其实“中国梵高”代表的是大芬村千千万万的画工,他和赵小勇只是刚好有幸拍了这个纪录片被当作代表而已。
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广场,赵小勇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寄出国的画作——那是一幅1.5m×1.8m的巨幅《向日葵》,显眼地摆在广场中央外国商贩的小铺上。
他记得那时,香港进口、50cm×60cm的画布要五块多;上海牌子、一管170克的马利颜料大概11块钱;猪鬃毛的油画笔便宜,只要一块多,但好的狼毫笔一支要50多块钱,每次画完洗干净,一把要用一年……
之所以这么“斤斤计较”,是因为从他们手中卖出的临摹画同样廉价。但是,售出几十块人民币的画作,经过包装,长途跋涉到达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后,身价甚至翻上几十番。
哪怕如此,这也已经满足这些画工的生活支出,甚至可以说“很不错”了。在当时,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能拿三四百的工资,“而我们在旺季的时候,每个月大概能有个四五千块钱。”
如今在周永久看来,流水线式的作品,可以叫作工艺,但不叫艺术。之所以采取这种流水线的方式,是迫于时间紧急。“说实话,我也并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,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又能赚钱养家,在当时已经很满足了。你叫我流水线工人也可以,说我是画匠也没问题。”
赵小勇则说,其实很简单,模仿就是赚钱,不要去讲其他的,因为要维持生活。“也没什么不好,因为是为了下一步的梦想。”
“我不是‘梵高’”
自从今年3月份居民基础养老金上涨后确定最低标准确定以来,根据不完全统计,已经有上海和北京地区上调了基础养老金标准。
后新冠时代,正值我国面临房地产下行、就业形势严峻、企业和消费信心下滑,以及地方债务激增和外部形势复杂之下,这场经济会议的召开,说小了说决定着我国未来五年的市场走向。
1991年,在周永久第一次见画画师傅时,从兜里掏出的是一张用铅笔画着荷花、鸳鸯、榕树、小鸟等图案的烟盒纸片。“还不错,可以培养。”师傅的这一句话,让他正式走上了画画的道路。
在1996年之前,周永久甚至不知道梵高是一个人,他以为是一种流派,自己笔下的也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画。2014年,当赵小勇在梵高博物馆第一次看到梵高真迹的瞬间,镜头里,他蹲在地上沉默了很久。
这些年,他们逐渐开始了自身“去梵高”的过程。在2008年,周永久意识到“临摹久了会被人定义”,于是开启了原创的道路,画自己想画的东西。
周永久最开始画的,是自己老家潮州的老房子。可是在那个“临摹世界名画”受追捧的年代,这些原创画作并不受欢迎。直到2008年9月某天,两个意大利客人踏进他的店。
“大批量订单几十块钱一张画,可现在能卖200块一张,我高兴得要命,11月份就交付了400张。”周永久感慨,这是被认同的荣耀感。
如今,赵小勇也同样执着于原创作品,香港街道、山水风景、过往经历……每一笔都源于自己的生活感悟。“虽然很难,但我正努力地成为自己。”他始终觉得,创作随心所欲,会更快乐,而临摹更压抑。“艺术追求是必然的,因为画画时间久了、技术提升了、眼界开阔了,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想去尝试画一些自己的作品。”
他说,每个人都是这样的,不只他一个。以前那种批量订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,这是整个时代的转变。
几十年过去,“中国梵高”的光辉和标签依然存在。或许,对周永久和赵小勇来说,成为“梵高”只用了几年时间,而成为他们“自己”则需要更久。但不管怎样,他们正走在这条“我不是梵高”的路上正规杠杆炒股公司,而且,已经渐渐走远……
发布于:浙江省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本站将立刻删除。




